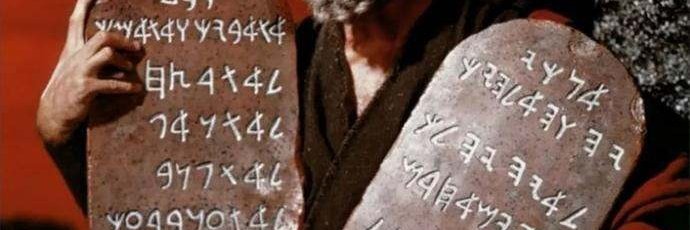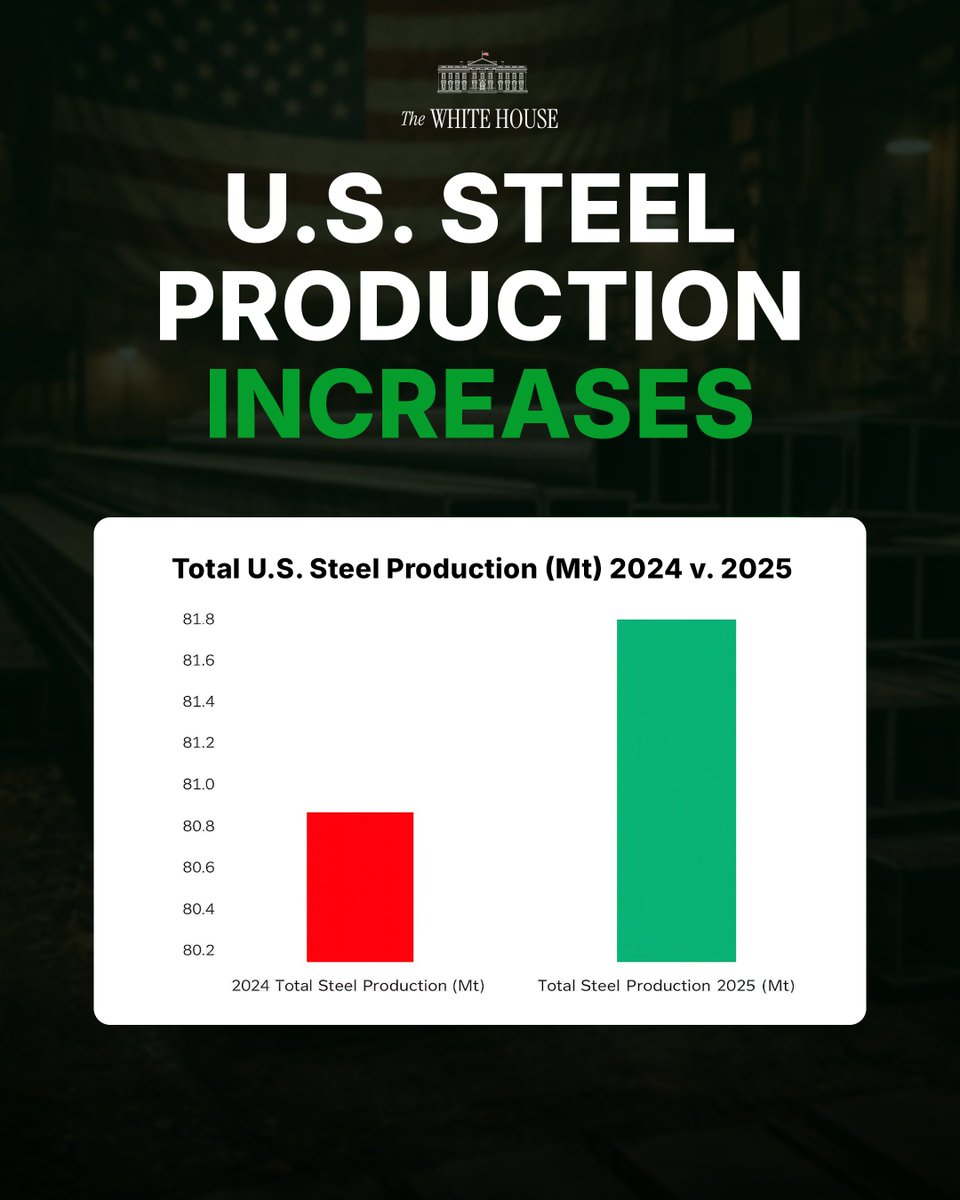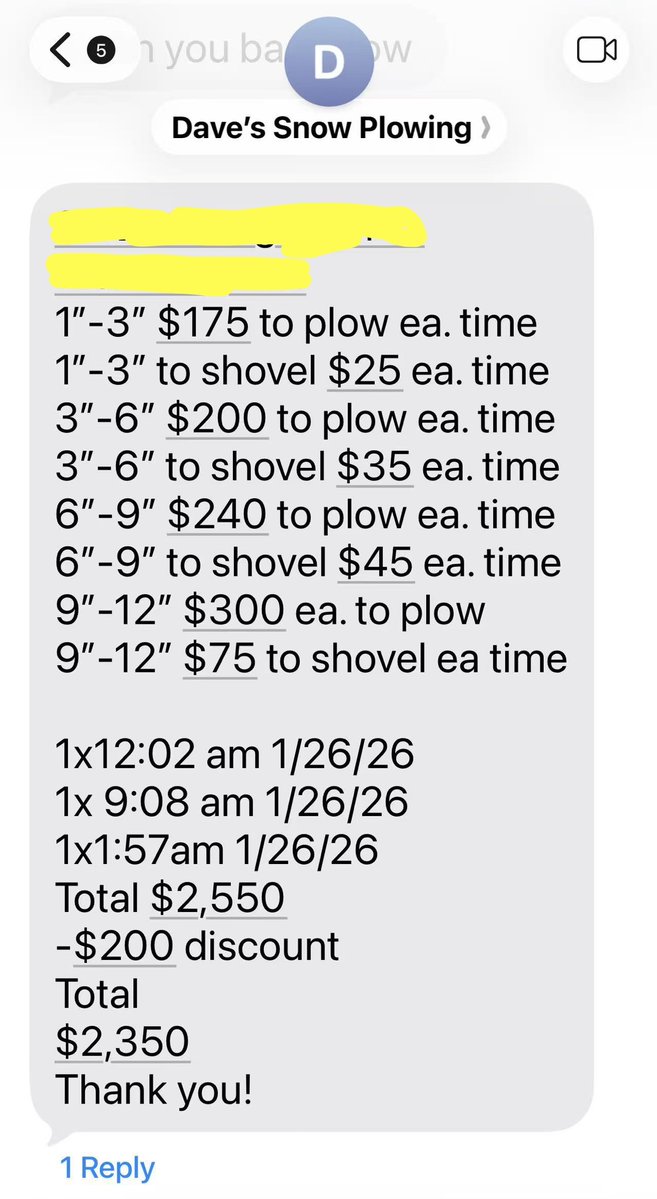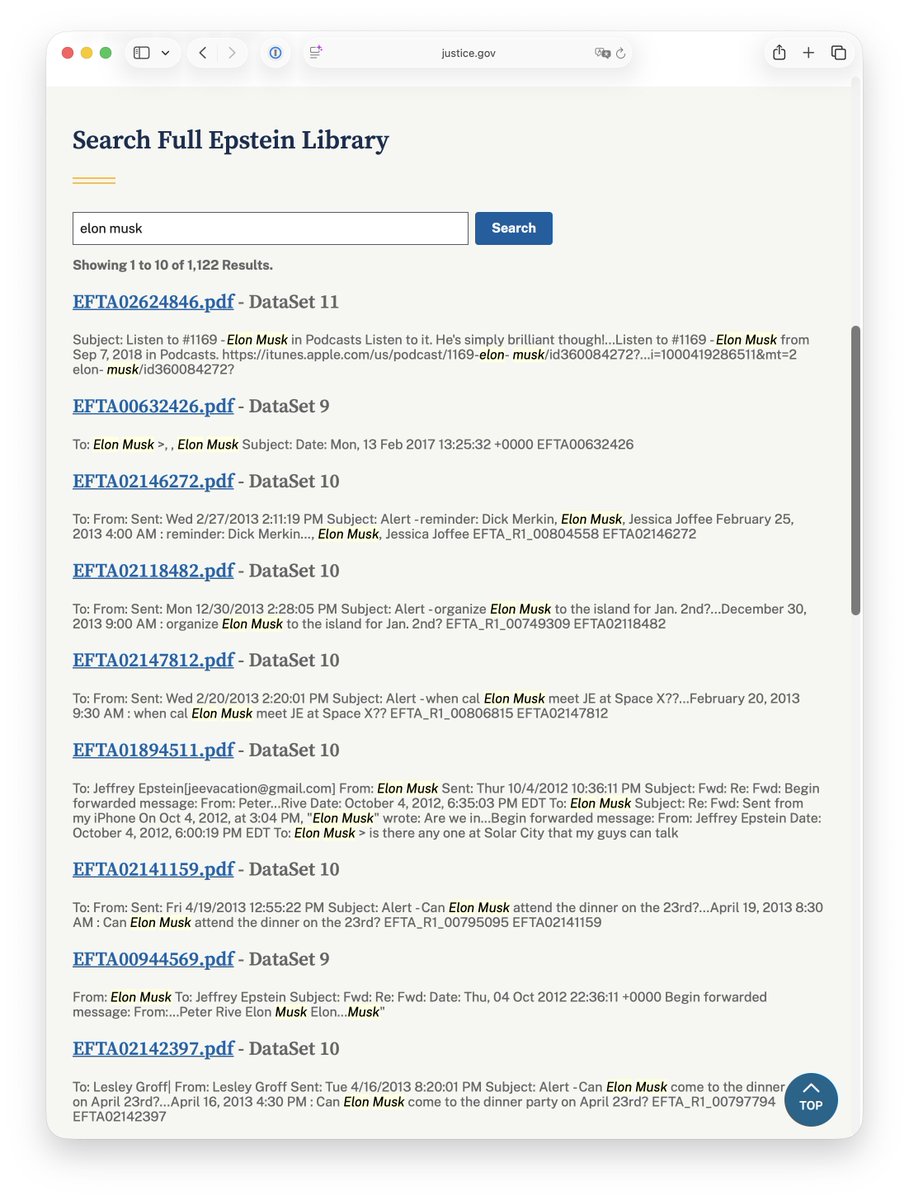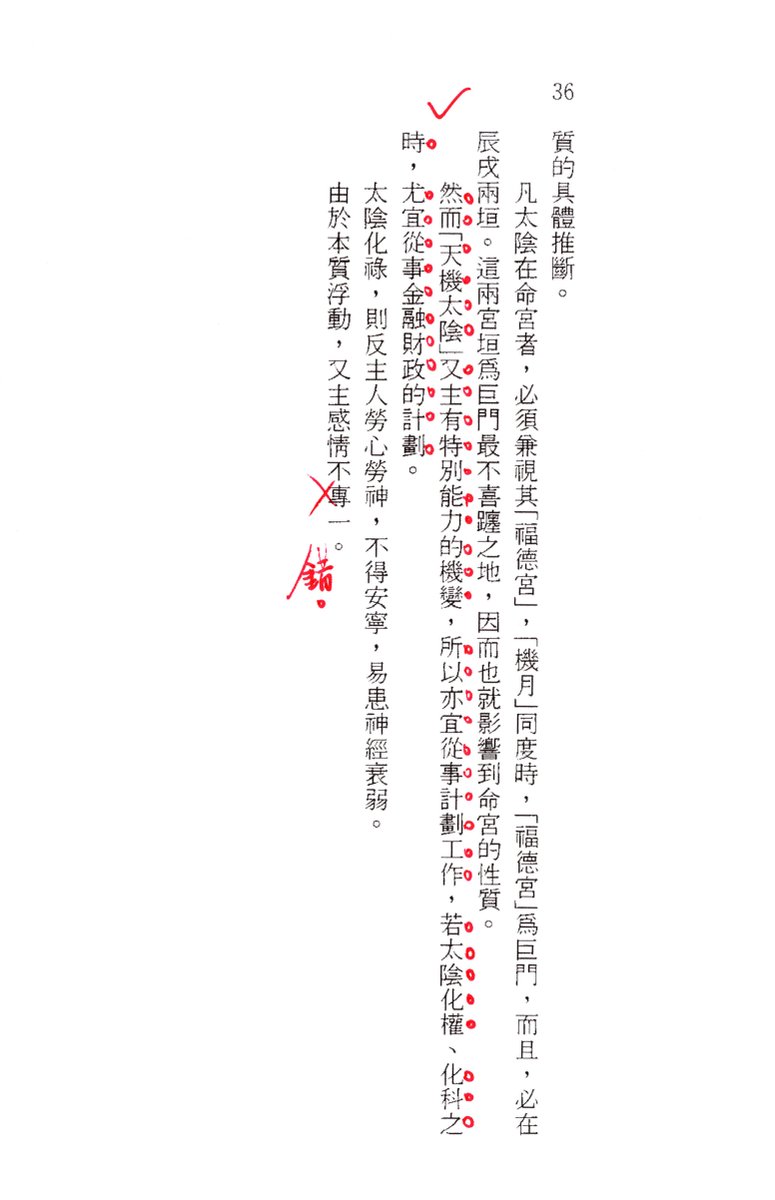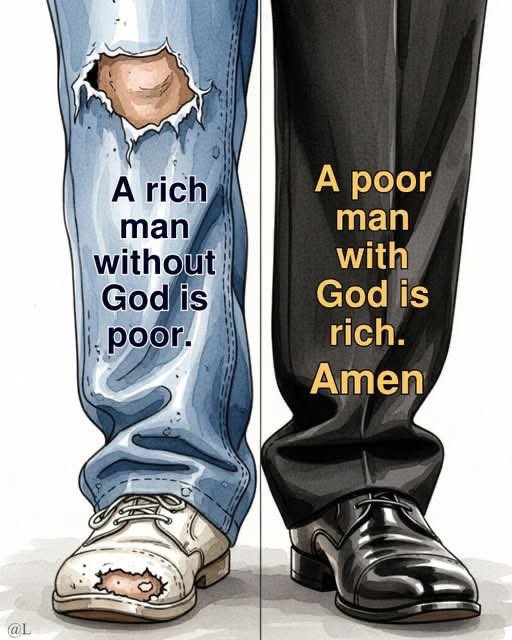《洋無能》
經常看到一個說法,就是說如果小孩是在美國、歐洲或者日本長大的,就比較單純,沒辦法去中國競爭,因為太複雜了。
實際上,這說法並不新鮮。
比如,很多偏遠山區的父母,都是這樣想的:我的娃從小在我們山溝溝長大,沒怎麼見過世面,太單純了,城裡怕是不能去,太複雜了!
同樣,很多人到歐美國家洋插隊,生了小孩,也在山溝溝或大農村長大,漸漸,對競爭更強的社會,一想起來就膽怯。
如果,一個中國的農村人,去中國的城市,發現競爭不過,甚至都不敢去,會被笑話這人不行。
如果,一個美國的農村人,去中國的城市,發現競爭不過,照顧面子的說法是:這孩子真太單純呀!
但不客氣地說:這是無能啊。
洋無能,就不是無能?
“單純”一詞,只在形容那種被虜獲的獵物、被馴化為供人把玩的寵物時,才算一個褒義詞。
但,對於一個成年男子,“單純”是一種羞辱。
善良很重要,但深謀遠慮、思考周祥、待人接物不像一截洋木頭,也是必不可少。
而且,即使在美國,“單純”也只是底層標配,甚至,只在你英語不好的情況下,你誤以為單純。了解越多,你會發現也不單純。不單純也就罷了,甚至還蠢。
再往上層看,即使在美國,食物鏈頂端,也都是些老狐狸。華盛頓不相信眼淚,華爾街不相信單純。你聽過“華爾街之羊”嗎?沒有吧,華爾街能活下來的,全是狼。
單純的人在哪裡?在愛心、鮮花、蠟燭、擁抱和祈禱,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
很多中慘階級父母說:“不希望我的孩子太複雜,還是單純一些好。”
果然如願,這些人的後代,看起來也傻傻的、楞楞的,一輩子聽人使喚,輪迴他父母輩的中慘命運。
在美國,你去銀行,那些腦子不太好使、賬也算不明白、中文也說不清楚的櫃員,就是最單純的華人二代,月薪三千,怎一個慘字了得。
而那些拼殺到食物鏈頂端的,不管華人、白人,沒一個簡單,沒一個傻白甜。想想看,貝佐斯、馬斯克、黃仁勛,哪個單純了?
在任何社會,單純只能被淘汰,成為別人的獵物。
把孩子養得傻白甜、毫無競爭力、幹啥都不行,那些做父母的,非但沒切腹認罪,竟然還驕傲起來了。
成年前,單純是好的品質。成年後,複雜才是好的。
複雜,就是同時處理多方面信息和多線程任務的高級運算能力,是一種活生生被文藝青年污名化的優秀品格。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張良,一點也不單純;神機妙算、老奸巨猾的諸葛亮,一點也不單純;就連作為西方人的馬基雅維利,哪裡單純了?作為成年人的我,多希望通過不斷學習,變得更加深邃、睿智、有謀略,或者說:複雜。
既然,我自己致力於成為一個複雜的人,適應各種環境,善巧無礙、隨宜應變,如庖丁解牛、游刃有餘,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我怎麼忍心自己的後代只是頭腦簡單的愛心鮮花蠟燭和擁抱的小綿羊?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一種能力。
“Love and Peace”,遲早找爹媽要生活費。
如果學貫中西,相當於腦子裝了雙系統,培養來培養去,最後竟然傻白甜、毫無競爭力、一個都不能打,還不如他爹,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難道我是教你詐?不,高維的單純,是世事洞穿後的此心光明,了無詭詐。但低維的單純,就是無知、無能,是腦子空空,是待宰羔羊。
別美化洋無能。
洋無能,也是一種無能。
得益於好萊塢的常年軟宣傳,以及世界各國上進人士因自卑而升起的美國崇拜,為美國這國家增添了不少情懷。
這就好像我們去一個地方旅遊,並不是為了看當地的房子、山脈或河流,而是為了感受某種情懷。定居和旅遊,也是差不多的,很多時候也是在為情懷買單。
比如說,如果你生活在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那裡的氣候基本上跟中國東北一樣,甚至暴風雪還更多,人人都凍得要死,房子也破敗得要命,湊合著過。
如果只用理性頭腦來看,就會感覺到冷,就會看到房子破敗,道路坑坑窪窪,電線桿在寒風中甩來甩去,哐當作響……但如果你事先被植入過某種情懷,那麼,你看到的就不是這些了。你會看到:新英格蘭的文化底蘊、你會看到傳統和現代的交織、你會看到愛默生曾走過的一段路、你會看到balabala……
再比如,即便到了 2026 年,你仍然需要每週手寫支票,疊好,放到信封裡,口水舔一下封好,再貼上郵票,寄到某地方支付一筆小額服務費。這事情,不能單用理性頭腦來思考,必須上一層情懷濾鏡。哇,傳統!哇,手寫支票的歷史感!哇,人與人之間可貴的信任……
不這樣上情懷的話,很多傻事就做不下去。
但如果有一天,這份情懷被打碎,那可就要不得了。
當那些《獨立宣言》中的廣告詞——「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被打破、被祛魅,被還原為它真正的廣告詞形態,問題就大了:路不好就是路不好,不是什麼歷史沉澱;房子破就是房子破,不是什麼文化遺產……
失去了濾鏡,狹義的旅遊業,和廣義的旅遊業,就不好發展了。
但如果有混球讓這些大詞祛魅、破壞這些情懷,那些深知這些宣傳大詞對美國不可或缺的老臣們,就紛紛驚呼萬萬不可——這完全是動了國本啊!
毫無疑問,這些老臣是頗有洞見的。
不能打破情懷,不能壞了濾鏡,不然就少了意思,真實就全露出來了。
幾年前,我們社區門前的十字路口沒有紅綠燈,只有雙向 Stop 標誌。車輛會自覺在 Stop 標誌前停一下,左右觀察後再走。一年總有那麼三四起搶道的意外,兩輛車撞在一起,但通常只是把前引擎蓋撞癟,問題不大。
“這麼繁忙的路口,全靠自覺禮讓,竟然不需要紅綠燈!”我常感慨,這在別的地方肯定行不通。
那時候,我每天開車送小孩上學,總看到旁邊有一些騎自行車上學的白人小孩。我就會想,自己是不是對小孩過於保護了?
但在 2023 年時,一位九歲小男孩在騎車上學途中,就在這十字路口被一輛福特皮卡撞死。
這事件讓我對「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產生了一些懷疑。
社區的愛心人士在遇難地點擺放了很多鮮花和蠟燭。當年的聖誕節,大家又想起這位小男孩,擺放的鮮花更多了,還拼出了他的名字,真的很讓人感動。
但孩子確實死掉了。
後來,社區才開了幾次會,決定還是要裝紅綠燈。我們都收到了信,工期一年半。
後來的一年半,總有一圈墨西哥工人在那工作。
我們社區有自己的雜誌,封面通常是鄰居中的一戶人家,拍得漂漂亮亮的,像廣告大片。
第二年,我在雜誌封面上看到了這小孩的父母。這家本來有兩個小男孩,現在一個被撞死了,還剩下另一個。照片中,他們夫妻摟著剩下的小男孩,笑得特別開心,這畫面讓我頗為震撼。
翻開正文,很少提到那位小男孩,通篇在說他們現在的家庭多幸福。而那位“被神接去”的兒子,他們很為他驕傲,因為整個社區都記得他的勇氣和卓越……
之前,我妻子總認為,這種事情發生後,他們肯定會賣掉房子,搬到別的地方去,不然怎麼忍心每天開車經過兒子被撞死的地方?
看了雜誌後,我告訴她,並沒有,他們很幸福,感謝神的恩典。我把雜誌遞給她,她擺手說不要看。
從那之後,即使社區的小男孩們紛紛把自行車換成速度更快的電動自行車、從身邊呼嘯而過,我也不再欣賞這種勇敢,也不覺得作為父母,在小孩還沒完全長成的年齡,盡我所能地保護他們有什麼問題。
不管怎麼說,我喜歡開車送小孩上學,和他們說說話,沒什麼不好的。
幾年前,我們社區門前的十字路口沒有紅綠燈,只有雙向 Stop 標誌。車輛會自覺在 Stop 標誌前停一下,左右觀察後再走。一年總有那麼三四起搶道的意外,兩輛車撞在一起,但通常只是把前引擎蓋撞癟,問題不大。
“這麼繁忙的路口,全靠自覺禮讓,竟然不需要紅綠燈!”我常感慨,這在別的地方肯定行不通。
那時候,我每天開車送小孩上學,總看到旁邊有一些騎自行車上學的白人小孩。我就會想,自己是不是對小孩過於保護了?
但在 2023 年時,一位九歲小男孩在騎車上學途中,就在這十字路口被一輛福特皮卡撞死。
這事件讓我對「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產生了一些懷疑。
社區的愛心人士在遇難地點擺放了很多鮮花和蠟燭。當年的聖誕節,大家又想起這位小男孩,擺放的鮮花更多了,還拼出了他的名字,真的很讓人感動。
但孩子確實死掉了。
後來,社區才開了幾次會,決定還是要裝紅綠燈。我們都收到了信,工期一年半。
後來的一年半,總有一圈墨西哥工人在那工作。
我們社區有自己的雜誌,封面通常是鄰居中的一戶人家,拍得漂漂亮亮的,像廣告大片。
第二年,我在雜誌封面上看到了這小孩的父母。這家本來有兩個小男孩,現在一個被撞死了,還剩下另一個。照片中,他們夫妻摟著剩下的小男孩,笑得特別開心,這畫面讓我頗為震撼。
翻開正文,很少提到那位小男孩,通篇在說他們現在的家庭多幸福。而那位“被神接去”的兒子,他們很為他驕傲,因為整個社區都記得他的勇氣和卓越……
之前,我妻子總認為,這種事情發生後,他們肯定會賣掉房子,搬到別的地方去,不然怎麼忍心每天開車經過兒子被撞死的地方?
看了雜誌後,我告訴她,並沒有,他們很幸福,感謝神的恩典。我把雜誌遞給她,她擺手說不要看。
很多事情,我們不能共情,但不管怎麼說,從那之後,即使社區的小男孩們紛紛把自行車換成速度更快的電動自行車、從身邊呼嘯而過,我也不再欣賞這種勇敢,也不覺得作為父母,在小孩還沒完全長成的年齡,盡我所能地保護他們有什麼過錯。
不管怎麼說,我喜歡開車送小孩上學,和他們說說話,沒什麼不好的。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姑且叫它:琥珀理論。
生活在美國的華人中,你會發現,來美國越早的,就越窮;來美國越晚的,就越富。
最富的,是剛來的。
當然,不是百分百如此,你可以找出很多反例,但從概率上講,我發現還真是這樣。
比如,如果剛成交一棟三千萬美金的海景房,門口停著勞斯萊斯,你絕不會認為,這是來美國三十年的華人買的。
不會的,你知道,這一定是新來的華人。
新來的才有錢。
來美國三十年的,你一眼就能看出來,他們的穿著打扮,還是和三十年前的人一樣,時間就停在那,價值觀也停在那,對中國的認識也停在那。甚至,聽的歌,也完全停在那。
像琥珀一樣,被定格在三十年前。
他們原先急著脫離的文化,其實像臍帶一樣給他們輸送營養,不斷更新,潛移默化。
但他們認為那不好,認為全都是劣根性,所以要嫁接一種更優越的文化,但問題就出在這,舊的斷掉的,新的接不上,一下就斷掉了。於是,營養斷供了,文化斷供了。
去唐人街,去老華人區,去華人教堂,就會發現,來得越早的華人,不管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都相對貧窮,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下一代也一臉茫然,一問三不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如果找了個好工打,聽印度人使喚的那種,爹媽就感謝神的恩典了。越窮的,越信教,越需要每週定期吸一口精神麻藥。
在貧窮的老華人區,英語說得好的,通常能找個工打,比完全不說英語的,日子要過得好一些。
在富裕的新華人區,英語說得好的,基本都是來得早的,通常是打工階級,撐不死也餓不死,但日子過得苦哈哈,寅吃卯糧,各種信用卡的返點了如指掌,保險的條款也看了又看,生怕出一件不能cover的意外,一下就返貧。
而那些新來的,幾乎不說英語,什麼都不懂的,還謙虛聽取老華人的生活經驗的,卻是最光鮮、最豪擲的。他們不是官員,不是腐敗分子,多數也是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他們自信打過很多勝仗,來這也一定能打下一片天地。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新移民也漸漸變成老移民,英語說得越來越好,感覺越來越融入了,越來越懂美國生活的小竅門,越來越會修馬桶,越來越會換廚房粉碎機,越來越會上房頂掃樹枝,越來越會車庫修卷閘門,甚至還買了皮卡,萬聖節在門口放墓碑……總之,越來越與他瞧不上的華人文化脫節,也越來越出局。
文化斷供,迅速風乾,成為標本。被遺忘,被凍結,成為琥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