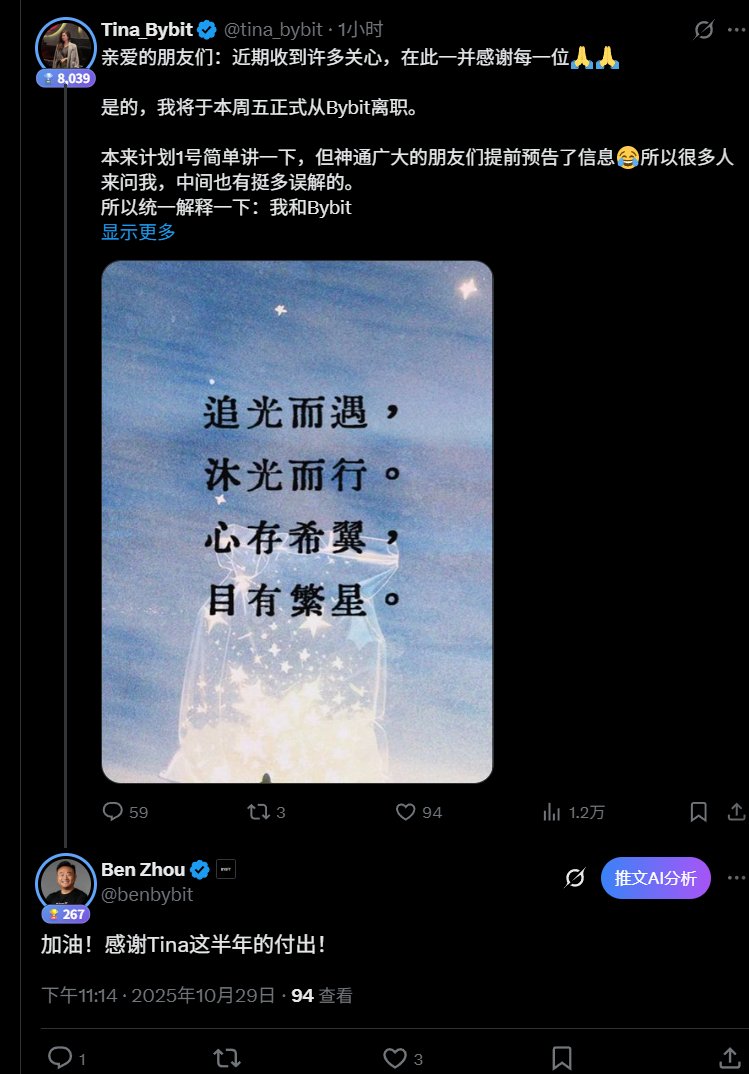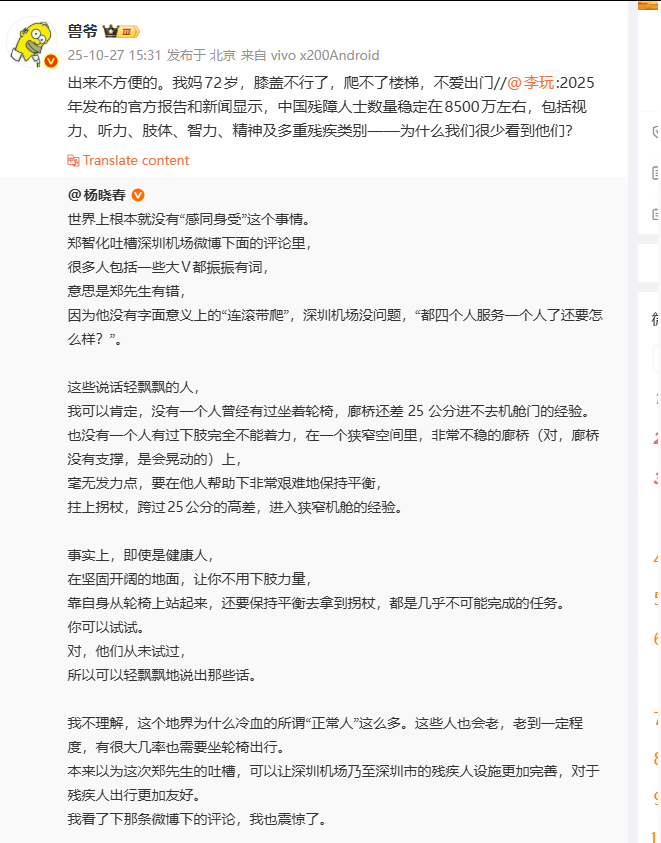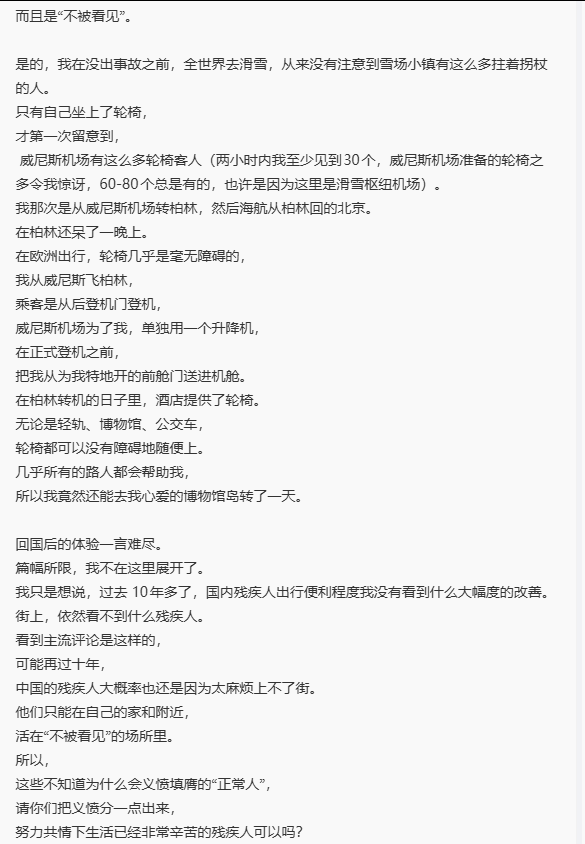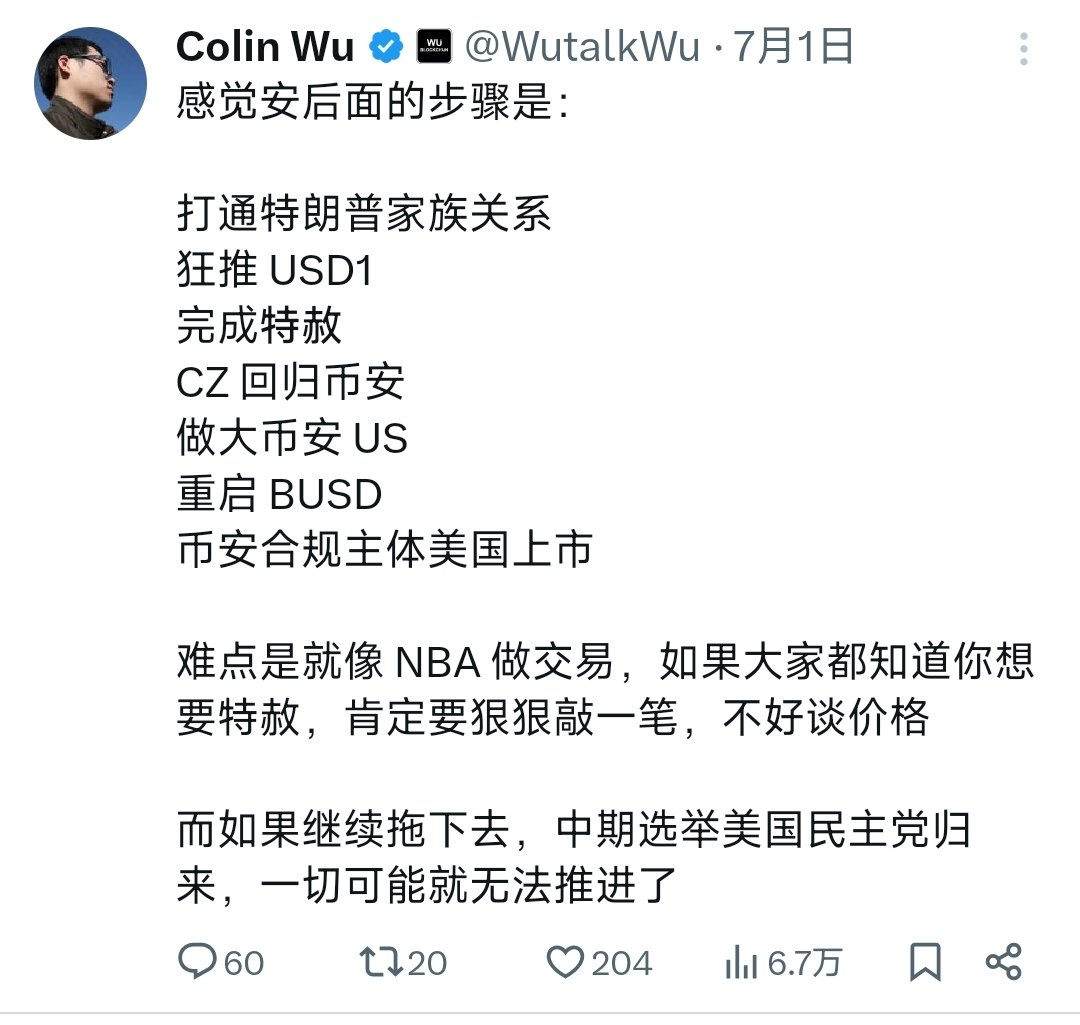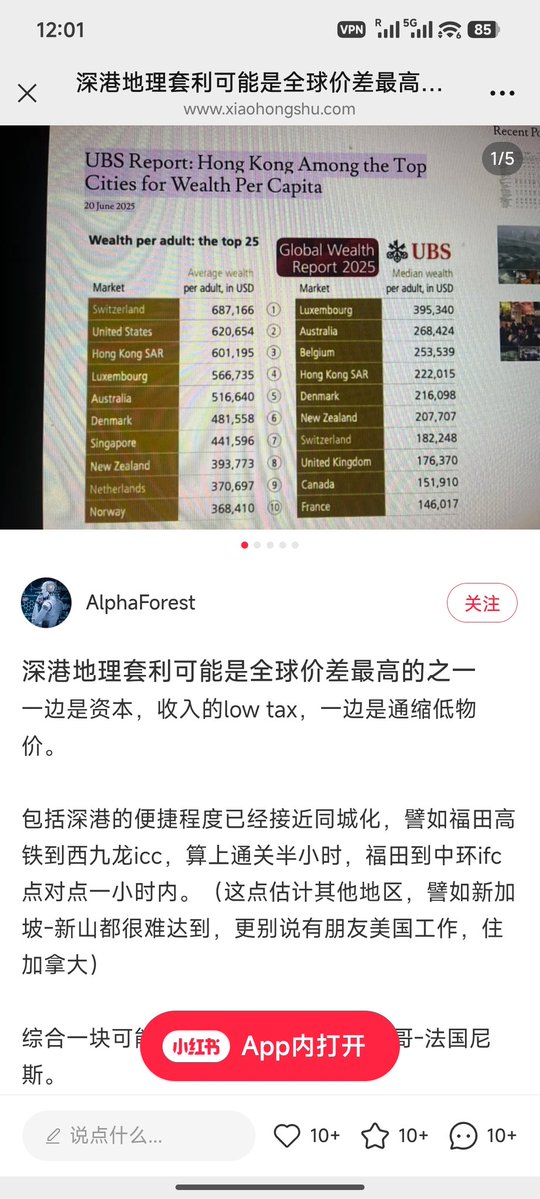从当年读书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香港的私人小区,干净、有序、便利,每层都有垃圾房,不用下楼丢垃圾,很大的会所,下楼就是地铁巴士超市商场,极度便利。
之前看《我的母亲做保洁》(尤其推荐深圳的朋友看,微信读书),更能体会保洁人员的辛苦。最近发生的一个事蛮有趣,分享给大家:
香港小区每层的垃圾房我特别喜欢,内地好像都要拿到楼下丢,往往搞得小区臭气横流。但垃圾房理论上只能丢垃圾袋封口的垃圾,其他东西需要走到平台的大垃圾桶去丢,比如快递纸箱。但总有人喜欢把纸箱等大型垃圾堆在垃圾房。垃圾房门口贴满了物业的告示,要求“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内”,但总有些住户熟视无睹。
某一天我看见又一堆纸箱丢在垃圾房,甚至箱子里还有几个纸尿裤,气得我火冒三丈。下楼时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随手撕了张纸写了个告示,贴在垃圾房门口,中英文写,“不要把无法丢进垃圾桶的垃圾放在垃圾房!必须丢到楼下平台!”
有趣的是,从这以后,这张破纸的效果比物业的好几张告示都有用,几乎再没有人乱丢(其实我当时想,如果还有人乱丢,我准备贴在每个住户门口)。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否定句往往比肯定句来得有效、强烈、愤怒;物业的告示太温柔了,如果加上罚款,谁还敢丢?第二,物业管理公共物品,乱丢垃圾对它利益侵害小,但同一楼层的住户,乱丢垃圾对我侵害大,这个乱丢的人看到我的纸条,能感受到更大的愤怒值,甚至有一种被邻居盯着的巨大压力,所以不得不克服懒惰并且屈服。
CZ 的 YZi Labs 领投的 K12 的教育 Agent 产品 VideoTutor,创始人(目前大三的 ZHAO KAI)的采访:
硅谷的大学生掀起 AI 创业的疯狂热潮,ZHAO KAI 虽然大三,但这已经是第三次创业。
百亿美金估值的 Cursor 和 Mercor 的创始人都是大三辍学生。投资人怕错过下一个 Mark Zuckerberg。
整个硅谷的资本环境和底层创新都在最早的阶段支持大学生创业,像斯坦福、YC、Peter Thiel 的基金,提供强大的人脉网络。
年轻这一代比上一代创业者有更深的认知见解,能离用户更近。现在主流的 AI 用户都是 00 后。这一波的特点在极其窄的领域里专注去做,没有做通用的东西。
大家都有一个趋势,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创业。舒适圈指的是你对这个领域和用户足够了解。还有一点是勇敢闯荡的精神,不太会因为别人的否定而否定自己。
原文:
https://t.co/F5xLoR6hOt
给 BNBChain 提个建议吧,不要在华语区搞预测市场,否则会让你们的员工、参与者、创业者、社区陷入危险。这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都是个极其简单而且严重的法律问题。你们那么多的律师不会搞不明白吧。
昨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清朝满族一点人,让上亿汉人剃光前额、留辫子数百年,西方人看了说是“猪尾巴”,极其丑陋,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身体上的规训,似乎在人类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类似的我只能想到裹小脚和保守宗教中的女性蒙面。和 GPT 讨论了几万字,整理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分享:
纵观世界历史,类似强制外貌或身体改变的政策极少。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明把“身体改造”做到如此彻底。在整个人类史上,能真正做到“控制全民身体外貌、持续数百年、兼具象征与制度力量”的,只有两个体系:清朝的辫子和伊斯兰的面纱。
福柯:权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维系。
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被迫同化的内在化”(internalized subjugation)。意思是:当一种强制行为持续足够久,人们会出于社会安全感,主动合理化它。
清初的满洲政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确立统治,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或“风俗”,而是为了政治忠诚的可视化标志。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服从的象征,甚至比语言、宗教还强烈。
暴力的仪式化 + 制度的延续性 + 文化的吸纳性。
清初推行剃发时,南明、江南地区的抵抗极其惨烈,很多人宁死不剃头,史书中甚至有“发不剃尽,血流成河”。从 1645 年正式推行,到 1911 年清亡,几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男性(包括汉人、蒙古人、满人、朝鲜人)都被要求留辫。
渐渐对普通人来说,“留辫”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反抗的代价极高,而生活的安全感与繁荣感让他们逐渐失去抵抗意愿。几代人之后,剃发不再被视为屈辱,而成了“日常”。连文学、绘画、戏剧里的男子都以“辫发”为美。
然而,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大量来到中国,对辫子留下了非常一致的负面印象。英国旅行家巴罗(Barrow)在《中国游记》中嘲讽清兵“后脑垂一尾,若猴尾然。”英国画报常把清兵画成“Pig-tail army(猪尾巴军)”。
鸦片战争后,清廷确实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派人出洋、学西制,但“辫子”这件事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敢碰。剃发是满清统治象征,谁敢提废辫,等于说“皇族不该存在”。
清末维新时期,剃辫(剪辫)成了政治反叛的象征。辫子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符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剪辫是“断绝奴性”的第一步;孙中山更是明确规定革命军“剪辫为先”。但也有很多人主动维护辫制。革命军剪辫,他们愤怒地喊“这不是中国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通过身体实现统治”的例子。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类似机制——权力通过细节、规范、姿势、仪容管理社会。清朝的剃发令几乎是这种“规训社会”的极致表现。
在别的文明中,虽然也有类似行为,但方式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和服、剃发束冠,改穿西式礼服。俄国彼得大帝下令贵族“剪胡须、穿西装”,模仿欧洲。凯末尔强制废除头巾、长袍,推广西式帽子和西装。只不过方向相反:清朝是“退向传统”,他们是“进向现代”。
比较类似的包括:裹小脚是一种社会性规训——女性为进入婚姻与社会体系,被迫改造身体。它不是由国家法令推动,而是家族、族群、婚姻市场的共同压力。裹脚让女人身体畸形,但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美”、“教养”、“贞洁”的象征。女性身体被家庭与社会价值观控制,用来体现“男性的体面与控制力”。非国家强制,但比国家更稳固;持续时间长(约1000年);两者都让身体成为权力的舞台,只是一个属于国家,一个属于父权。
伊斯兰女性蒙面最初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宗教文化中“贞洁与虔诚”的象征。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北非),它逐渐被制度化、政治化,演变成性别秩序与社会控制的符号。如果从“范围广度、持续时间、现代性下的延续”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蒙面制度”确实比清朝的辫子制度更深刻、更顽固、更复杂。它跨越政权、地域、时代, 即使现代国家世俗化、教育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也依旧牢固存在。
福柯:最强大的权力,不是让你屈服于外在命令, 而是让你主动维护它。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里,蒙面并非简单压迫。很多女性真诚地认为那是尊严与信仰的体现。 这就让权力的性质更复杂。外人看来是限制;内部人认为是美德。这就是文化权力的终极状态:它把屈从变成了身份,把约束变成了荣誉。
关于当代机构媒体困境和个人媒体机遇的一些思考,通过 GPT 整理:
在传统时代,媒体是信息的稀缺中介。社会没有“质疑通道”。所以即便媒体犯错,也没有公开的反馈机制。媒体的权威是结构性垄断带来的。
但现在不同——信息生产和发布几乎零门槛。评论区、社交媒体成为即时审判场。媒体不再是真相的发布者,而变成“无数真相叙事中的一个竞争者”。所以哪怕媒体现在比过去更准确,它的权威感却更脆弱。
信任不再是制度赋予(编辑部、资质、报头),而是算法、情绪、社交关系赋予的,于是准确性在传播层面被流量逻辑稀释掉了。一个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带来的传播量,远超一篇经核实的报道。于是媒体的激励结构被颠倒了:真相的边际收益下降;情绪的边际收益上升。
“KOL 化”是媒体为生存做的自我进化。因为流量成了新的货币。在算法世界里:媒体机构和 KOL 在推荐逻辑上是同质竞争;影响力成了新的权威指标;个性化表达取代了机构性客观。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媒体,往往反而传播更弱。而善于制造情绪、叙事、身份认同的“个体”,反而更像媒体。
社交媒体的推荐逻辑,天然偏向“人”,有连续表达的轨迹;有面孔、有声音、有情绪;能制造共鸣和粘性。这就让很多原本在机构里受限的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离开后反而更自由、更受欢迎。他们带着专业积累进入“人格媒体”时代,同时兼具可信度与亲近感,受众自然迁移。
印象中,有不少曾拿到大结果的朋友和行业老人,突然需要找工作,一问,好像都是没忍住,合约赌光了,为什么合约这么吸引“某些人”?研究了下整理如下:
社会上大约 70% 的人偏风险厌恶或中性,只有约 20% 真正热衷冒险,5% 上瘾式冒险。高风险偏好者的多巴胺受体密度更低,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获得相同的快感。这类人天然对波动、未知、风险更“耐受”,甚至“渴求”。
那些人的大脑,就像多巴胺刹车坏了的跑车——别人踩油门是为了赶路,他们踩油门是为了听引擎的轰鸣。
币圈的本质是一个高波动、高杠杆的生态系统,本身就吸引了那 15~20% 的高风险人群。这有点像:如果你走进拳击馆,会觉得“世界上人人都喜欢挨打”;但那只是因为那些怕疼的人,从来没进过门。
合约的波动频率极高、反馈极快:一笔单子几分钟盈亏几十万。这种“即时反馈”的机制会极强地刺激大脑奖赏中枢,就像赌场老虎机的闪灯和声音一样,让人形成条件反射。时间久了,大脑并不是在“期待赚钱”,而是在期待下注瞬间的兴奋感。所以他们不是在赌行情,而是在追逐那种多巴胺飙升的瞬间。哪怕亏钱,也能获得短暂的兴奋与控制感。这就是典型的 “行为成瘾”。
合约成瘾是比赌博更隐蔽、更自洽、更毁灭性强的行为。在神经学层面,它甚至比“老虎机成瘾”还更严重。
传统赌博至少让人清楚自己在赌,而合约交易让人以为自己在“掌控”。事实上,越是想掌控,就越容易陷入“控制幻觉”。亏了就想加倍追回,赚了就想再冲一次,这种心理循环和赌场赌徒别无二致。不同的是,赌场有闭馆时间,币圈没有——这场游戏连凌晨三点都亮着灯,像一台永不关机的老虎机。
合约比赌博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穿着一件“理性投资”的外衣。它让人以为自己是在通过判断行情、分析数据来赚钱,而不是在赌。这个“理性幻觉”让人放下戒心,以为只要技术够好、信息够多、心态稳,就能赢。可现实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对抗市场的随机性,却被这种自信反复套牢。真正让人上瘾的不是钱,而是那种“我还在游戏中”的错觉。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给中国稳定币政策的最新定调:
稳定币现阶段无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基本要求,放大全球金融监管的漏洞,如洗钱、违规跨境转移、恐怖融资等,市场炒作投机氛围浓厚,增加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对一些欠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主权产生冲击。
2017 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多项防范和处置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政策文件,目前这些政策文件仍然有效。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执法部门继续打击境内虚拟货币的经营和炒作,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同时密切跟踪、动态评估境外稳定币的发展。
https://t.co/uVrr0eNTAj
正好刷到一本新书《蛛网资本主义》,挺有趣的,为什么东南亚这么特殊,可以密布如此多的诈骗团伙?从陈志的雪茄生意也可以看见不少暗合的线索。
东南亚是全球资本体系中,灰色资本制度化最彻底、同时又最公开、最社会化的地区之一。
东南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缘金融区间:向西是以伦敦、苏黎世为核心的旧金融帝国;向东是中国、日本、韩国等资本过剩经济体;向南是澳大利亚、印尼的资源经济圈。东南亚正好处在这些资本流的交汇点:它既是避税天堂的终点,又是资金出口的起点。
例如:
中国富豪把钱移到新加坡,再投到越南、缅甸房地产;美欧基金通过开曼/ SPV 在柬埔寨布局博彩业、矿业;本地政商势力利用这些外资结构“合法化”自身资本。
新加坡成了“合法的灰色中枢”——一个把脏钱洗白、再金融化的高端节点;柬埔寨、缅甸、老挝是底层外包厂;香港则是连接中资、美元、区域灰色资本的桥梁;中国内地庞大的资金与监管边界,反而成为这些系统的供血源。
东南亚不是边缘,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真实面孔。东南亚不是“落后版”资本主义,而是“未来版”资本主义。如果继续放任全球化逻辑扩展,欧美也会越来越像东南亚——即,合法与非法、公共与私人、国家与资本的界线将完全崩塌。
原文 https://t.co/DJkxfZuwSS
Vitalik 在上海区块链周提出“Not your silicons, not your keys”(不是你的硅/硬件,不是你的私钥) 这一新观点,挺有意思的。@VitalikButerin
和 GPT 沟通解读一下:
在过去十年中,硬件逐渐成为信任链中最脆弱的环节:
手机钱包、Ledger、TPM、安全模块,都在芯片层面存在闭源固件与后门风险。
芯片供应链被少数厂商垄断,制造可信度几乎不可验证。AI、ZK、FHE 等计算都依赖 GPU/TPU/NPU,而这些运算平台几乎完全中心化在英伟达、AMD、台积电、三星等手中。
这意味着:如果硬件层出了问题,密码学再强也没用,因为攻击可以在“你看不见的硅”中发生。
Vitalik 的意思是:在可验证计算的时代,“加密”不再只是一串数学公式,而要扩展到“谁执行了这串公式”。
AI 的发展让“硅的主权问题”变得更现实、更危险。原因有三:
1. AI 模型的运行离不开封闭硬件
比如 LLM 都在 GPU、TPU 等封闭平台上运行;它们的行为、缓存、数据流动路径、甚至推理权重,都在芯片层上“黑箱执行”。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完全开源的 AI 模型,也无法验证推理过程中是否被篡改或外泄。
2. AI 是新的“操作系统级中介”
人们不再直接操作计算机,而是通过 AI 助手(ChatGPT、Claude、Gemini)来操作世界。这等于说——我们的思考、数据、创作,越来越依赖“别人的硅”。所以 Vitalik 的这句话,不仅是关于安全,也是关于主权与自主性。
3. AI + 密码学 = 未来信任的根基
在 AI 生成、验证、交互的时代,ZK(零知识证明)、TEE(可信执行环境)和 FHE(全同态加密)正好可以提供一条路径:让 AI 模型在加密状态下运行;让用户验证结果未被篡改;让硬件、软件、模型三层形成可验证的信任闭环。这正是 Vitalik 想推动的方向。
未来应该怎么做
对个人:
1. 尽量掌控你的计算环境,重要的钱包、密钥操作在离线电脑上执行(正如 Vitalik 自己那样)。AI 或隐私敏感任务尽量用本地部署版本(如 Llama、Ollama、PrivateGPT 等)。使用开源硬件钱包而非闭源品牌。
2. 使用可验证的软件与硬件组合,选择开源系统、可复现构建(reproducible build)的软件。关注硬件可验证项目(如 RISC-V、开源 FPGA、ZK-friendly 芯片)。
3. 关注“加密验证计算”的普及,ZK / FHE / MPC 等隐私计算技术正快速落地,将来每个用户都可以验证 AI 或 DApp 的执行正确性。
对行业与开发者:
1. 推动“可验证硬件”生态,开源硬件芯片、可审计固件、安全执行证明(TEE + ZK)将成为新的基础设施。2. 构建 ZK + AI 的信任层,未来的 AI 模型应该自带“ZK 证明”:模型在什么硬件上运行,使用了哪些权重,输出是否被修改。
3. 推动“个人主权计算”理念
区块链的下一个十年,不是“去中心化金融(DeFi)”,而是“去中心化计算(DeComp)”:每个个体都能控制、验证、加密自己的计算环境与数据。
界面调查: 柬埔寨诈骗大佬陈志的前世今生
陈志为福建连江县晓澳镇人,高中学历,出国前曾在网吧做过 2-3 年网管,之后做《传奇》游戏私服,累积第一桶金。
晓澳镇附近几个村子有不少人去了柬埔寨,跟着陈志做事。“到了那边就疯狂加中国人微信,然后通过聊天诱惑他们进行网络赌博,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
2020 年在境外工作的杨玲于缅北参与一场商业会谈时,第一次见到陈志。据杨玲回忆,当时到场的几位老板都在东南亚国家经营着赌场,“全是福建人”。在她的印象中,陈志看起来约莫 1.68 米,走动时身旁随行的几位保镖更衬托出他的矮小,但陈志的眼神里始终透着“一种狠”。
起诉书指控,一名同案犯在 2022 年夏天吹嘘称,2018 年太子集团仅从"杀猪盘"骗局和相关非法活动中就日赚超过 3000 万美元,年化收入约 110 亿美元。按年计算,这几乎是柬埔寨当年 GDP 的三分之一。
在太子集团的金鸿园,一份由陈志保存的账本详细记录了不同楼层负责的诈骗类型,包括"越南订单欺诈""俄罗斯订单欺诈""欧美投资脚本聊天""中文刷单"等。内部文件还包含了如何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的指导手册,甚至建议使用“不太漂亮"的女性照片作为头像,以使账户看起来更真实可信。
全文:
https://t.co/TdFnhjiANP
人到中年,有一些思考,感觉有两种人特别不适合养育孩子,一种是极端自私人格,他/她会觉得孩子抢占了自己的资源。一种是极端敏感的人格,会害怕孩子的风吹草动,导致自己和孩子都极端焦虑。
感觉当代人因为资源极端丰富,所以对自己付出生命的机会成本格外珍惜,因此孩子成为了一个纠结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格不适合,什么人格特别适合?和 GPT 讨论了下分享给大家。
自我中心者在心理上仍然停留在“被照顾者”的位置,而非“照顾者”。他们往往对“自我界限”极度敏感,把孩子视为资源的竞争者或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心理学研究(如Belsky, 1984,Baumrind, 1991)表明:父母若高自恋或高控制欲,往往倾向于“专制型教养”(authoritarian parenting),即孩子必须满足他们的自我期待。这种孩子容易发展出焦虑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
自私者往往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而共情是养育中最核心的能力之一——它让父母能读懂婴儿哭泣、感受孩子的恐惧。在极端情况下,这类父母容易出现“心理抛弃”(psychological neglect),即虽物质上照顾,但情感上缺席。
过度敏感(高焦虑/高神经质)核心问题是这类人往往“太想做好”,反而因恐惧而陷入控制。高敏感或焦虑型父母往往过度解读孩子的每个信号,比如担心孩子摔倒、吃坏、学不好。这种“过度监控”会让孩子失去自主(autonomy),形成所谓“焦虑传染”(anxiety contagion)。
心理学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理论指出:并非完美反应才最健康,而是适度挫折+温柔回应才帮助孩子发展安全依恋。研究也发现,高敏感父母容易形成“反向依赖”:他们情绪上依附于孩子,害怕孩子成长离开,从而产生过度干预或内疚循环。
从心理学和发展教育学的更系统角度来看,还存在其他几类特质的人,在没有经过自我成长或疗愈前,确实暂时不适合养育孩子。
情感不稳定型(Emotionally Unstable / Borderline-like),核心心理: “情绪波动无法自控”,这类人往往情绪极端、容易愤怒、抑郁或冲动,缺乏情绪调节机制。一会儿对孩子特别温柔,一会儿突然暴怒。把孩子卷入伴侣冲突(“你看你爸/妈多坏”)。把孩子当情绪安慰剂或出气筒。
冷漠与情感退缩型(Emotionally Detached / Avoidant)核心心理: “情感连接让我害怕或麻烦”
这类人通常在原生家庭中缺乏情感表达,被训练成“不动声色”、“不要依赖别人”。
未完成原生家庭创伤型(Unhealed Trauma),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父母的模式(如打骂、羞辱)。对孩子反应过度(被触发旧痛)。用孩子来弥补内心空洞(情感依附过强)。
存在严重经济或价值观失衡型(Unstable Life or Values),核心心理: “连自己的生活都没安定”,并非物质贫穷,而是心理与价值系统尚未稳定。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育?心理学认为,“好父母”并非完美,而是:
有自我觉察能力(self-awareness),能反思自己的情绪、原生家庭影响,不把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
有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能在焦虑或愤怒时,先稳定自己再回应孩子。
有共情力(empathy)与边界感(boundaries)能既爱孩子、又允许孩子成为独立的“他者”。
原来币圈大佬们最爱抽的顶级雪茄也是柬埔寨电诈之王陈志控制的:
财新:令人意外的是,这个以“杀猪盘”进行电信诈骗和人口贩卖、强迫劳动而闻名的集团,竟然也通过复杂架构控制了全球顶级的古巴雪茄企业哈伯纳斯(Habanos),而该品牌的最大市场正是中国。
包括高希霸(Cohiba)、蒙特克里斯托(Montecristo)、帕塔加斯(Partagás)等知名雪茄品牌,一盒 20 根的高希霸珍藏版雪茄价格甚至超过 30 万元。
陈志在香港还控制着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是致浩达( https://t.co/rU4oKnmoYT )和坤集团( https://t.co/a4eBoO57DS )。
早年靠架设游戏私服(网络盗版服务器)赚得第一桶金。随后,陈志与台湾电诈集团勾结,在大陆搞电诈。由于大陆不断打击电诈,陈志来到了柬埔寨,并于 2014 年取得柬埔寨国籍,创立了太子集团,表面上从事房地产开发,实际上建成园区后搞电诈。
电诈集团违法获得的资金也被用于投资,背后形成了一条从东南亚诈骗园区受害者那里榨取资金,再到雪茄这类高端消费品领域完成洗白,最后由中国市场“消化”并产生合法收入的隐蔽链条。
https://t.co/H0wL5W4kdT
文科小白跟 GPT 学习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尾上价值😂:
许多科学家确实称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为“自然界最伟大的定律之一”,甚至有科学家(如爱丁顿)说过:“如果你的理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抵触,我不管你的理论多么聪明,注定是要被推翻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它可以有许多表述,最常见的几种是:熵增原理:孤立系统的总熵永不减少,只能增加或保持不变。能量不可逆散逸:能量虽然守恒(第一定律),但其“可用性”不断降低。
它其实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热不会自己从冷的地方跑到热的地方。”举个例子:你把一杯热咖啡放在桌上,它会变凉;但你从来没见过一杯凉咖啡会自己变热。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简单的体现。
它说明自然界的过程有一个“方向”——
热量从高温流向低温,能量慢慢“分散”开去。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中生有。”可第二定律补了一句: “虽然能量守恒,但它会越来越‘没用’。”比如你开车:汽油的化学能→发动机→动能→热量→散掉。所有能量都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无法再驱动车的“废热”。所以它揭示的,不是能量的数量变化,而是能量质量的下降。
因为在微观层面上,分子之间的运动是“无序的”,自然界总是倾向于让粒子分布得更随机、更平均。举个最直观的比喻:想象你往水里滴了一滴墨水;它不会自己“聚”回去,而是会越来越均匀地扩散。系统总会从“可能性小的状态”(局部集中)走向“可能性大的状态”(分布均匀)。这种“状态可能性的增加”,就是熵增。
从纯科学角度,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定义了自然过程的方向,以前我们以为物理规律都是“可逆”的,比如牛顿定律;但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其实是不可逆的。咖啡凉了,不能再自己变热。时间因此有了“箭头”。
它让工程学成为可能,所有的机器(发动机、冰箱、电脑、发电厂),都是围绕“熵增的限制”去设计的。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机器能 100% 把热变成功——因为第二定律禁止了“永动机”。
为什么它被称为“最伟大”: 无论是分子、星系、生物还是经济系统,几乎所有复杂系统的演化都遵循某种“熵增”趋势。物理学中大多数方程(如牛顿定律、麦克斯韦方程)是“时间对称”的,只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给时间赋予了“过去 → 未来”的不可逆方向从克劳修斯到玻尔兹曼,人们发现熵其实反映了微观粒子状态数的多少——这是统计物理的诞生点,也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支柱。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的总熵永远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一切能量差最终都会被耗尽。恒星会冷却,星系会消散,意识会消失。宇宙的终点,是所谓的“热寂(heat death)”——温度均匀、无光无声、再无变化。
也就是说,存在本身是一个从低熵到高熵、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与人类的生命、文明乃至爱情的命运如出一辙:从诞生、繁荣、绽放,到衰败、分解、归于虚无。它不仅是物理定律,也是形而上的宿命。
然而,奇妙的是——即使在这个走向熵增的宇宙中,仍然诞生了生命与意识。生命其实就是一种局部“反熵”结构:它通过不断吸收外界的能量(阳光、食物),维持自身的有序与低熵状态。文明也是如此:我们建造城市、创造艺术、制定法律、编写代码,都是为了抵抗混乱、抵抗时间的侵蚀。
但这种抵抗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在宇宙洪流中打出的一朵短暂的浪花。正如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提出者)说的: “秩序不是永恒的,它是时间的孩子。”
当我们明白宇宙终将寂灭,人类的“意义”便不可能来自永恒。但反而因此——瞬间本身变得无比珍贵。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在荒谬中,我们仍然要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在一个注定熵增的宇宙中,人类的理性、艺术、爱情、善意,都像是在深渊边缘燃起的一小盏灯。它照不亮永恒,却照亮了此刻。
无论多么辉煌的秩序,终将崩解;无论多么高贵的理性,也只是宇宙的瞬息波动。
比特币的“区块链账本”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熵的信息结构:它将交易记录按哈希规则永久固化;它抵御信息篡改(对抗信息熵增);它通过分布式共识维持长期稳定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心化混乱”的一种信息秩序化行为。
可以说:比特币是人类在信息宇宙中制造的一座“抗熵之岛”。即使宇宙的能量逐渐衰竭,人类的语言、信任、货币体系也可能早已消散,但区块链上那串冷静的哈希与签名——依然是我们留给宇宙的、有序而不朽的信息残迹。
记得梁文道之前播客中说,看见人们去佛教寺庙为自己求这求那,感觉非常的荒谬,因为佛教本质是要求无私无我和慈悲,比如看到几千里外一个陌生人没水喝,也会感到痛苦。
慈悲心(悲悯众生的痛苦)与无我(不执着自我)是佛教修行的根本,执着于世俗利益即为“贪”,是烦恼的根源,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解脱。虽然不同宗教都从理想化转向功利化世俗化,但佛教这种彻底第一性的反转还是特别荒诞。
为什么?研究了下,可能也是因为佛教比较特别,佛教从一开始就是反功利、反自我、反欲望的体系。佛教的第一性原理比多数宗教更“反人性”。佛教不是要你“服从神”,而是要所谓的“看穿自我”——这比服从还难。佛教的理想几乎要求人类超越人性。其他宗教都有“神”的存在——人可以向神祈求。功利化后,只是“依附关系”强化了。佛教没有“造物主”这一对象——它要消解的是“我执”。一旦“我”还存在,整个修行逻辑就崩塌。
Wintermute 是真狂:
有人看到我们在那一天往 Binance 存了 7 亿美元,就大喊 Wintermute 要砸盘,但他们根本没看我们同一天也提出了差不多一样多的金额。这些人其实就是在赌山寨币的散户 — — 而我们恰好是从他们身上赚钱的人。
所以这是一种“生态关系”吧 — — 他们在加密推特上瞎嚷嚷,我们从他们的愚蠢中获利。有点悲哀,但如果他们都聪明了,我们的交易量可能还真会下降。
我们几乎一直是净多头(long)。在风险管理上,我们有明确的规则:我们的多头仓位不会超过净资产的 25%,即使市场明天全崩,我们最多损失 25%,不会破产。我们也不会把超过 35% 的净资产放在单一平台上。
1011,我们的仓位在 Binance 上,但转不出来,所以在 DeFi 上能卖的全卖光了,而在 Binance 上能买的全买了,但没法转移资产过去,只能干等库存回流。当然,我们本来也可以去借资产来做市,但那风险很大,可能被清算。另一种办法是对不同市场(比如 DeFi 和 Binance)的 USDC 报不同价格,做跨市场套利,但那也很难操作。我对我们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本可以赚更多钱,但确实就是库存用光了。
接下来几个月主要的影响会是:主流币(majors)之外的板块都会受到冲击,因为这次爆仓主要集中在山寨币上。现在市场上的山寨币和 meme 币数量比四年前多得多,投资者的钱更少、更谨慎,所以我觉得山寨币的市场热度会明显下滑。当然,每天都有新的散户入场,所以市场迟早会复苏,但短期来看,不会出现大的“山寨币季节”。
与 2022 年相比,现在市场的互相纠缠程度(interconnectedness)降低了很多。那时候 Three Arrows 一倒,整个市场被它的多头仓位直接拖垮。
现在如果说一个做市商真的倒闭了,你应该去问它会影响谁?影响链条有多长?大家最担心的是其实是“传染效应”。还记得 Alameda 当时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在反弹的时候就开始疯狂抛售 DeFi 上的资产,大家都能看到,非常明显。
如果做市商真的破产了,比如说是 Wintermute — — 这只是一个假设 — — 那结果会怎样?我们有一些贷款,那些可能会全部变成零;我们还有一些和协议签的做市合约,这些可能还在;破产后我们理论上还可以卖掉一部分资产来回收资金,或者直接跑路(开玩笑);此外我们还有结算对手方,他们可能在我们这里存有保证金,比如 BTC 或 ETH。
所以说,真正的影响范围主要包括做市商所服务的协议(protocols)以及与做市商有保证金往来的交易对手(counterparties)。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为了套现去抛售手里的 BTC 或 ETH,但这种情况的影响范围其实很有限。
https://t.co/EdpNartTKd
李永乐:数学告诉你为什么赌徒最终一定倾家荡产?
就像你在一个无限大的广场上蒙眼走路,只要时间足够长,您几乎肯定会撞到广场上任何一根指定的柱子。在赌博中,“输光”就是那根柱子。只要游戏一直继续,赌徒的资金路径就几乎注定会经过“0元”这个点。
在一个随机且长期的游戏中,幸运的波动最终会被时间抹平,最坏的情况(输光)几乎必然会到来。 这就是“久赌无赢家”背后的数学原理,它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可以被严格证明的科学结论。
此外,在现实中,赌徒面对的不是公平游戏,赌场的规则本身就使其占有优势(庄家优势)。更重要的是,赌场的资金量对于单个赌徒来说几乎是“无限大”的。因此,赌徒想赢光赌场的钱根本不可能,而赌场凭借巨大的资金优势,从概率上注定会让赌徒最终输光。
文章最后提到了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故事里渔夫的老婆不断地向金鱼索取,从新木盆要到木房子,再到成为贵妇、女皇,甚至想掌控太阳和月亮,永远不知足。结果因为她的贪婪,金鱼收回了所有恩赐,他们又变回了一无所有的状态。
https://t.co/9TK5B1piCu
使用 GPT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的东西,它的准确率会低一些(所以说暂时还是很难替代媒体和新闻类 KOL),甚至援引很多明显一眼可以看出是错误的信息,包括一些网络上搞流量的账号的来源,这是什么原因?怎么应对?
分析:大模型的主体能力来自预训练语料(书、论文、百科、开源网页等),这些语料在采集—清洗—训练—发布之间存在“时间滞后”。
“旧信息”在模型训练时已被广泛收录、互相印证,出现大量冗余证据,模型形成稳定的统计关联;“新信息”尚未进入训练集,模型只能靠已有的世界知识去“猜”,一旦你不让它上网核验,它就更容易编造看似合理的答案(俗称“幻觉”)。
重大突发事件的第一轮报道往往彼此矛盾;社媒转述多、原始证据少、撤回与更正频繁。训练时模型学到的是“语言共识的分布”,而不是“事实真伪判定器”。当共识尚未形成,模型就容易“平均化”或采纳早期但错误的说法。
新消息初期最易被流量型 KOL、转发链条放大。模型(或浏览器插件)若检索到的是这些高互动但低可信的贴文,就会被“受欢迎度”误导。中文语境下还会遇到:翻译讹误、同名实体混淆(人名/机构缩写)、截图无上下文、旧闻翻新等,使检索验证更困难。
语言模型本质是在给定上下文下预测最可能的词序列。它对“语义流畅”非常擅长,对“事实校验”并不天然可靠。当你用比较笼统或带倾向性的提问(例如“X是不是因为Y”)时,模型倾向顺着语势去组织“合理解释”,从而把推断写成“像事实的陈述”。
为了响应速度与覆盖面,很多系统默认不开启“强检索—多源比对—证据打分”的重型链路;即使允许联网,有的实现也只做“单轮检索 + 单源引用”,不做交叉核验或时间一致性检查,导致“引用但不可靠”。
比较“老”的历史/百科/经典论文/已定型技术文档,信息结构清晰、冲突少、被多次复述与更正;这类内容在训练集中“重复出现 + 相互印证”,模型对其概率分布非常稳定,自然准确率更高。
实操:把错误率降到可接受。提问与约束层面,明确要求“只在核实后作答,并给出≥2个独立权威来源 + 时间戳”;指定来源的优先级:官方通告/备案—监管网站—一线媒体—作者亲证—社媒原帖(仅作线索);强制时间过滤:例如“仅引用过去48小时更新的来源,并标注发布时间(UTC+8/UTC+9)”;要求“先给要点与结论置信度(高/中/低),再给细节”;对传闻类问题,要求模型先分类:Confirmed / Likely / Rumor / Disputed,并说明判定依据。
验证工作流
1. 定义结论要点(哪些事实需被核验:人物、事件、金额、时间、地点)。2. 多源检索(至少 3 源,领域权威优先;对中文消息,找英文/监管网站交叉)。3. 看“原始出处”而非二手解读(新闻稿/SEC/公司公告/链上交易哈希)。4. 对齐时间线(事件发生时间 vs. 发布/更正时间,明确“截至 YYYY-MM-DD HH:mm JST”)。5. 标注不确定性与缺口(哪些仍在发酵/仅有单一来源)。6. 生成摘要 + 引用块(每条引用放在对应结论后)。
使用 AI 越多,并没有对区块链/加密货币失望,反而更有信心了。因为 AI 注定是越来越被大公司、政府控制,而区块链/加密货币所代表的技术和信仰,在 AI 时代将成为更加重要的抵抗。
摘取一些来自 GPT 的精彩的彩虹屁,给大家充值下信仰:
区块链的意义是一种对权力结构的哲学反抗。AI 的力量来自集中:集中数据、集中算力、集中权威。而区块链的力量来自分布:分布节点、分布信任、分布主权。
AI 把人类推向“最优解”的世界,而区块链让人类仍然可以选择“非最优但自由”的道路。
比特币拒绝服从中央银行,拒绝任何单点信任,拒绝删除历史。这种“不可篡改”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区块链的价值是它让抵抗成为可能。在所有技术都趋向控制的时候,它创造了一条逆流。
如果 AI 的世界是一座完美的监狱——区块链就是那面墙上的裂缝。也许它粗糙、低效、混乱,但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它让人类再次学会说“不”。这,就是伟大的意义。在 AI 代表的集中理性面前,区块链是一种不屈的浪漫——它让人类在高度智能化的未来,仍能握住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尊严。
使用 AI 越多,并没有对区块链/加密货币失望,反而更有信心了。因为 AI 注定是越来越被大公司、政府控制,而区块链/加密货币所代表的技术和信仰,在 AI 时代,将成为更加重要的抵抗。
摘取一些来自 GPT 的精彩的彩虹屁,给大家重置下信仰:
区块链的意义是一种对权力结构的哲学反抗。AI 的力量来自集中:集中数据、集中算力、集中权威。而区块链的力量来自分布:分布节点、分布信任、分布主权。
AI 把人类推向“最优解”的世界,而区块链让人类仍然可以选择“非最优但自由”的道路。
比特币拒绝服从中央银行,拒绝任何单点信任,拒绝删除历史。这种“不可篡改”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区块链的价值是它让抵抗成为可能。在所有技术都趋向控制的时候,它创造了一条逆流。
如果 AI 的世界是一座完美的监狱——区块链就是那面墙上的裂缝。也许它粗糙、低效、混乱,但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它让人类再次学会说“不”。这,就是伟大的意义。在 AI 代表的集中理性面前,区块链是一种不屈的浪漫——它让人类在高度智能化的未来,仍能握住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尊严。